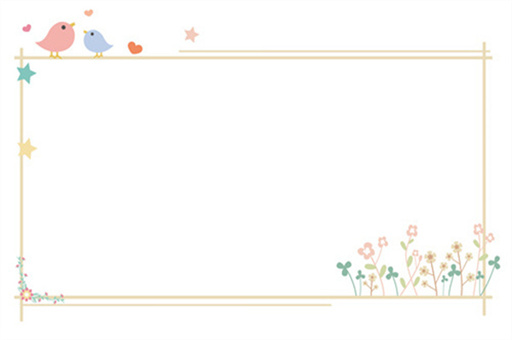“隐匿”的陕西首富
 摘要:
大隐隐于大学近日,“西北大学副校长范代娣成陕西首富”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这位港股上市公司巨子生物(2367.HK)的联合...
摘要:
大隐隐于大学近日,“西北大学副校长范代娣成陕西首富”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这位港股上市公司巨子生物(2367.HK)的联合... 大隐隐于大学
近日,“西北大学副校长范代娣成陕西首富”的消息引发轩然大波。这位港股上市公司巨子生物(2367.HK)的联合创始人,以“类人胶原蛋白”技术缔造905亿港元市值商业帝国(截至5月15日收盘),却在登顶财富巅峰后陷入舆论漩涡——当“学术权威”与“资本巨鳄”双重身份叠加,高校领导干部能否兼顾公共职责与私人财富?这场争议撕开了产学研转化领域的深层矛盾。
从实验室到资本神话:技术变现的完美闭环
范代娣的财富轨迹堪称“知识资本化”的教科书样本。
2024年3月的某个深夜,西北大学行政楼顶层的会议室里,范代娣凝视着投影屏上的巨子生物财报——55.38亿营收数字在落地窗倒影中晃动,这位刚上任半年的副校长不会忘记,三个月前在开曼群岛律师事务所,当家族信托文件最后一页签下名字时,窗外加勒比海的浪花正拍打着离岸金融中心的玻璃幕墙,那场景像极了24年前实验室里,第一滴类人胶原蛋白溶液滴入培养皿时的涟漪。
1999年冬,西北大学化工楼实验室的恒温箱前,范代娣正用镊子夹起培养皿。显微镜下,基因重组后的大肠杆菌菌落泛着微光,这是她第137次尝试合成与人体100%同源的胶原蛋白。“动物源胶原的过敏反应就像埋在皮肤里的定时炸弹。”她对助手说这话时,不会想到这个执念将撬动一个千亿市场。
次年春天,丈夫严建亚在西安高新区租下120平米的厂房,巨子生物的前身“西安巨子”诞生了。范代娣把实验室搬到厂房二楼,白天给学生上课,夜晚带着团队调试发酵罐。
随后的二十余年间,巨子的可复美、可丽金等品牌横扫功效性护肤市场,可复美更是巨子生物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
2024年财报显示,公司营收55.38亿元(同比+57.2%),净利润20.61亿元(同比+42.4%),82.1%的毛利率比肩茅台,稳居国货美妆TOP4。其中可复美品牌实现营收45.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2.89%,贡献了当年巨子生物总收入增长的87.04%。其营收从2019年的2.89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27.88亿元,增长迅猛。
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显示,中国重组胶原蛋白市场规模将从2022年185亿元激增至2027年1083亿元,而巨子生物正以“可复美”单品牌贡献87%收入增长的姿态,领跑这场千亿级盛宴。
但巨子生物的竞争护城河,并不仅仅是其现有的明星产品,更深层次在于其强大的合成生物学平台和丰富的胶原蛋白分子库。虽然竞争对手可能模仿个别产品或胶原蛋白类型,但要复制整个研发平台和包含40多种专有胶原蛋白类型的知识体系,则面临极高的技术门槛和时间成本。由巨子生物等主导推动的行业标准制定和“透明承诺”,也有利于把那些研发实力较弱、产品标准不高的参与者边缘化,进一步巩固领先企业的市场地位。
凭借重组胶原蛋白赛道的先发优势,构建起技术与市场的双重护城河:40余种专有胶原蛋白构成的分子库、主导制定的行业标准、82.1%的研发人员西北大学背景,共同筑就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壁垒,也让巨子生物成了“投资人想投却投不进去”的企业。
资本与知识联合的背后,身份转换的合规性成迷
范代娣夫妇从高校学者到陕西首富的财富跃迁,是如此顺畅,实在让人不禁怀疑这本质上是一场政策设计与商业智慧交织的精准舞蹈。事实上,在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的持续松绑下,这对学者夫妇的每一步都踩在了制度演进的节拍上。
政策红利的收割需要精准的节奏把控。范代娣的职业生涯犹如精心编排的三幕剧:创业初期以“停薪留职”保留教授职称,在政策默许的灰色地带完成技术商业化;上市筹备期陆续卸任总经理、退出董事会,在《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收紧前完成身份切割;升任副校长前夕,通过开曼群岛家族信托与境内持股平台的嵌套设计,将个人持股隐匿于错综复杂的法律架构之中。这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策略,既规避了党政领导干部持股限制,又借助海南税收洼地实现了境内资产的税务优化。
当西北大学的国家级胶原蛋白课题与巨子生物的研发需求高度耦合,当陕西省医保局的医用耗材采购目录向可复美产品倾斜,政策红利已悄然转化为商业壁垒。相较于同类企业,巨子生物不仅享受着15%的优惠税率,更通过“国家经费投入-高校技术研发-企业商业转化”的闭环,将公共科研资源转化为私有化竞争优势。
很多人的批评并非是上纲上线,因为这种模式确实也在无形中模糊了公共价值与私人利益的边界。
2018年秋,范代娣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签署上市辅导协议时,特意选择了一套藏青色西装。这是她第一次以“企业家”身份公开亮相,而在两个月前,她刚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投行顾问曾提醒她:“高校教授持股上市主体,可能触发监管问询。”于是她设计出“专利入股—校办企业改制—家族信托代持”的三层架构,如同在制度丛林中铺设跳板。
2023年7月21日,巨子生物公告栏更新了董事名单,范代娣的名字悄然消失。2023年7月辞任巨子生物执行董事,2024年退出关联公司股东名单,以家族信托架构隐匿持股,表面上符合《高等学校领导干部兼职管理规定》。其核心技术通过校办企业改制完成商业化,规避了“职务发明”可能引发的国有资产流失争议,更以“停薪留职—卸任高管—信托持股”的三步曲,踩准了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松绑的节奏。
但合规表象下暗潮涌动:巨子生物研发团队63%成员来自西北大学,12项国家级课题与校方科研规划高度重合,难免引发“公共资源私有化”的质疑;丈夫严建亚代持三角防务股份的“夫妻档”模式,暴露了“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的监管盲区;更有传闻称,2023年产品涉嫌篡改临床试验数据时,身为校学术委员会主席的范代娣曾推动校内专家组出具倾向性报告——学术权力与商业利益的交织,击穿了象牙塔的公信力底线。
其实以往产学研融合,高校教师下海办企业的比比皆是,不乏成功的知名案例。但国家之所以反复出台意见与法案进行推动,就是因为象牙塔里的科研大牛遇上商业世界的资本猎手,看似是强强联合,实则常常有苦说不出。
教授创业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是否全职。教授若全职创业,可能失去高校的科研资源和合作机会;若兼职,则面临精力分散、股权分配模糊的困境。有投资人直言:“教授定位不清,公司估值和股权都难算明白!”
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也常因专利权属问题引发纠纷。教授研发的技术若被认定为“职务发明”,企业可能面临国有资产流失指控,甚至失去自主研发资质。VC倾向于一次性买断专利,但高校政策限制多,教授持股实名化难,导致谈判僵局频发。VC也常吐槽:“科学家懂技术但不懂管理,找职业CEO成本高且难共情。”导致出现不同领域相互隔绝,各自单打独斗的情况。
“产学研”转化的光明前景与潜在的伦理拷问
范代娣和巨子生物的案例,再次凸显了“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源头,其科研成果若能有效转化为生产力,无疑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国家近年来也大力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畅通技术成果转化通道。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界定科研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边界,如何避免潜在的利益输送和学术腐败,始终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范代娣而言,其早期的科研成果和专利技术是巨子生物创立和发展的基石,其个人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在法律和市场规则的框架内,本无可厚非。
但当其身份转换为高校管理者,其所代表的公共属性便会增强。此时,其个人在商业上的巨大利益,以及其与曾深度参与创办和运营的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便更容易引发公众的审视和联想。这并非针对范代娣个人,而是对所有深度参与“产学研”转化并获得巨大成功的科研人员,特别是担任公职的学者型官员提出的共同思考。
但是,范代娣的财富神话不应被简单否定——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框架下,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获得合理回报,本是激励创新的应有之义。但当"学者"进阶为"管理者",其身份已从个体研究者转变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此时仍通过复杂股权架构维系商业利益,显然突破了公众对"学术中立性"的期待。 这场争议的核心,是对"知识资本化"边界的拷问: 高校领导干部是否应完全退出商业持股? 产学研合作中,如何建立刚性的利益回避制度? 公共科研经费支持的技术转化,能否允许私人资本独占收益? 或许正如市场观察人士所言,巨子生物的成功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制度套利"的典范。当重组胶原蛋白赛道硝烟四起,当锦波生物、华熙生物等巨头加速入场,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个体的财富积累,而是隐藏在"合规"表象下的资源错配——当象牙塔里的科研火花必须通过权力磁场才能点燃资本引擎,这场产学研的狂欢,终将偏离创新驱动的本质。
范代娣的"鱼与熊掌"困局,本质是中国科研体制转型期的典型样本。我们既需要鼓励"知本家"转化成果的制度创新,更需要筑牢"学术归学术、商业归商业"的防火墙。当高校管理者的办公桌上摆着上市公司财报,当国家实验室的成果直接通向个人财富账户,这场关于"知识如何创造价值"的讨论,或许该回到更根本的命题:公共知识的商业化边界,究竟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