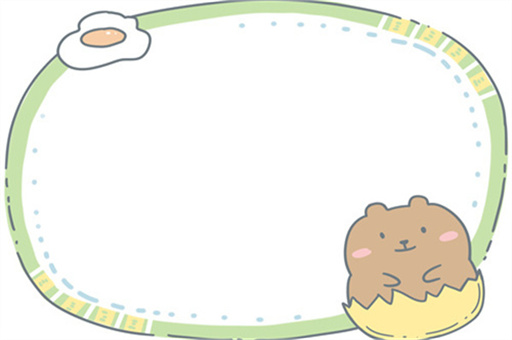辉瑞血亏撤退,罗氏断腕,强生放弃,千亿赛道谁还敢“赌”?
 摘要:
图源:豆包基因疗法正在迎来最强的“冰火两重天”。火的一端是,这种具有“一次性治愈”的疗效而被誉为天花板是“神药”,依然吸引着无数制药企业及资本的蜂拥而入。冰的一...
摘要:
图源:豆包基因疗法正在迎来最强的“冰火两重天”。火的一端是,这种具有“一次性治愈”的疗效而被誉为天花板是“神药”,依然吸引着无数制药企业及资本的蜂拥而入。冰的一... 图源:豆包
基因疗法正在迎来最强的“冰火两重天”。
火的一端是,这种具有“一次性治愈”的疗效而被誉为天花板是“神药”,依然吸引着无数制药企业及资本的蜂拥而入。
冰的一端是,包括强生、福泰、罗氏、辉瑞、武田、渤健在内,这两年在基于腺相关病毒载体(AVV)的基因治疗药物这条赛道里弃子“逃跑”的MNC,已经多到一只手数不过来了。
并且进入2025年,逃离AAV基因疗法竟然不再是新鲜事。仅过去一周,强生与福泰两家公司前后脚地宣布放弃AAV基因疗法的相关开发,再往前追溯,罗氏重组基因疗法子公司Spark,辉瑞彻底退出基因疗法……种种“利空”给AAV基因疗法的未来蒙上了一层又一层阴影。
巨头齐落跑,AAV成“烫手山芋”
全球制药一哥,竹篮打水一场空后,正在快速撤离AAV基因疗法赛道。
近期,强生旗下潜在同类首创的AAV基因疗法bota-vec治疗X连锁视网膜色素变性的III期LUMEOS研究失败。bota-vec是一种在研基因疗法,它利用腺相关病毒将视网膜色素变性GTP酶调节蛋白(RPGR)基因的功能性拷贝传递到视网膜,旨在通过修复突变基因,改善患者的视力状况。尽管该研究结果“具有方向性支持”,但未能达到主要终点。
强生一直对bota-vec寄予厚望。2023年底,强生以6500万美元的首付款,4.15亿美元交易总价,从MeiraGTx手中获得bota-vec的全球权益。如今试验失败,不仅前期投入的大量资金打了水漂,还可能影响强生未来在眼科基因疗法领域的布局。
对强生来说,这一失败算得上是个不小的打击。
而几乎在强生宣布III期临床遇阻的同期,另一家深耕基因疗法的罕见病巨头福泰制药,也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却也情理之中的决定——宣布将停止使用腺相关病毒(AAV)作为基因治疗载体的研究。
其实福泰停止使用常用于基因治疗药物封装和递送的腺相关病毒载体技术已有先兆。今年2月末,福泰已经终止了与Verve Therapeutics的一项最初于2022年展开的合作,合作为期四年,原本包括预付款和里程碑付款在内的交易总额达到了4.66亿美元。而彻底放弃AAV技术平台则意味着至少还有两家AAV相关合作企业可能受到波及。
若再往前数,罗氏、辉瑞、武田、渤健,原本跑在前面的制药巨头们,一股脑地在AAV基因疗法这条赛道里踩了刹车。
辉瑞可以算是今年逃离基因治疗最彻底的MNC。今年2月时,辉瑞将用于治疗B型血友病的AAV基因疗法Beqvez撤市,这款产品是2024年4月26日才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B型血友病的,定价高达350万美元。只是上市还不到一年,由于市场需求疲软,自获批以来未有患者接受商业化治疗,如今被辉瑞直接放弃了。
而辉瑞在基因疗法的撤退,可以从2023年开始算起,彼时,辉瑞将早期基因治疗项目和相关技术以10亿美元的价格打包出售给了阿斯利康的罕见病部门Alexion。到了2024年6月,辉瑞研发的治疗DMD的基因疗法Fordadistrogene movaparvovec III期临床失败,辉瑞直接放弃了该疗法的后续开发。2024年末,辉瑞又宣布终止与Sangamo Therapeutics合作的A型血友病基因疗法giroctocogene fitelparvovec的开发……
而至今年Beqvez产品撤市,辉瑞已经没有处于商业或临床阶段的基因治疗产品,从2014年便在基因疗法这条赛道真金白银投入长达十年之久的辉瑞,终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另外,巨头罗氏,最近正对旗下基因治疗部门Spark Therapeutics进行“根本性重组”。Spark Therapeutics是罗氏在2019年以溢价125%的收购而来,创下了当时基因疗法领域的最大金额并购案。只是短短五年后,罗氏不得不忍痛求变。
与辉瑞放弃Beqvez如出一辙,罗氏的重组也离不开商业化受阻的因素。早在2017年,Spark的全球首款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基因疗法Luxturna获批,但到了2023年其销售额暴跌59%,仅有约2000万美元。罗氏也直言“Spark的未来收入与协同效应均无法覆盖其账面价值。”
对Spark根本性重组的举措不仅让罗氏付出了24亿美元的成本,还导致337名员工失业,剩余310名员工被并入罗氏母公司。
由此来看,让MNC不顾过去多年重金投入也要撤退的原因都能归结至两大核心:“走不出实验室”的研发困阻与“跑不通”的商业化枷锁。
不及预期的十字路口,至暗还是黎明前?
相较于研发端的败走麦城与撕不开商业化口子的困局,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这一领域依然有热钱不断涌入。
当然这也离不开过去几年AAV基因疗法的的确确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自20世纪60年代首次被发现以来,AAV从实验室的“潜力股”成为基因治疗领域进展最快的疗法之一,多个产品成功获批上市,持续在市场上掀起投资热潮。
2012年11月,由UniQure公司开发的用于治疗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 (LPLD) 的Glybera (alipogene tiparvovec) 在欧盟获批,成为首个正式上市的AAV基因疗法药物,也开启了基因疗法的新时代。
截至目前,全球已有9款AAV基因疗法正式获批,给无药可用的罕见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算得上迄今为止商业化最为成功的基因治疗药物,诺华的Zolgensma诞生于2019年,用于治疗2岁以下的小儿脊髓性肌萎缩症(SMA),其采用AAV9载体递送SMN1基因,通过单次静脉注射将功能性SMN1基因导入运动神经元,实现长期SMN蛋白表达。自获批以来销售额逐年增长,在2021年实现了约13.51亿美元的销售额,并在随后几年均保持超10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成为首款该类别的重磅药物。
中国公司也不甘落后。2025年4月,中国信念医药的波哌达可基注射液(商品名:信玖凝,研发代号:BBM-H901)获批上市,用于治疗血友病B(先天性凝血因子Ⅸ缺乏症)成年患者。这是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AAV基因治疗药物,通过静脉给药将人凝血因子IX基因导入血友病B患者体内持续表达,从而提高并长期维持患者体内凝血因子水平,以期达到“一次给药、长期有效”的治疗及预防出血效果。
据统计,近年来全球 AAV 基因疗法领域的投资持续增长,众多药企纷纷布局,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相关研发项目。一些专注于AAV基因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如Spark Therapeutics、Regenxbio、uniQure等在资本市场备受青睐,股价一路攀升,不断获得高额融资用于研发管线的拓展和临床试验的推进。各大制药巨头也纷纷通过合作、并购等方式涉足AAV基因疗法领域,这些举措进一步推动了AAV基因疗法市场的发展,使其成为生物医药领域最热门的赛道之一,一时间风光无限。
虽然不能简单的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形容,但AAV基因疗法的火热,也成了孕育“危机”的温床。“热钱”涌入带来管线井喷,可随着研发进程的推进乃至商业化时,越来越多可能“人财两失”的问题也暴露出来。
今年3月,Sarepta Therapeutics公司用于治疗杜氏肌营养不良症(DMD)的基因疗法Elevidys出现首例治疗相关死亡病例,该患者在接受Elevidys治疗后因急性肝衰竭(ALF)死亡。Sarepta股价也应声暴跌27%。
Elevidys是一款基于腺相关病毒载体(AAVrh74)的重组基因疗法,由Sarepta和罗氏联合开发,于2023年6月获FDA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针对DMD的基因疗法,价格与其他基因疗法类似,都是百万美元的天价。
数据显示,在高剂量AAV(超过2×10¹⁴vg/kg)给药下,Elevidys有可能引发胆汁淤积性肝炎,这与2020年安斯泰来AT132治疗X连锁肌管肌病(XLMTM)临床试验中出现的3例死亡事件所揭示的数据相符。此外2022年,诺华也报告了两名患儿在接受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Zolgensma治疗后,因急性肝功能衰竭而发生的死亡。患者死亡事件再次把基因疗法的安全性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
摆在AAV基因疗法,或者说整个基因治疗面前的另一个鸿沟则是无人买单。就像产品获批也撂挑子不干了的宇宙大药厂辉瑞现身说法的——太贵了,医生和患者都不感兴趣。
更是有基因疗法领域先驱蓝鸟生物这种,艰难支撑到商业化,还是先驱变先烈。今年2月蓝鸟生物宣布被全球投资公司凯雷(Carlyle)和SK Capital收购,估值仅为2900万美元,要知道蓝鸟昔日市值曾高达百亿美元。
让蓝鸟生物加速“死亡”的,正是产品上市后不佳的表现。蓝鸟生物的三款基因治疗产品,分别针对地中海贫血、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和镰状细胞病。但产品无法盈利成了压垮蓝鸟生物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分析指出,安全性风险,叠加每剂200万-300万美元的天价,让基因疗法的风险收益平衡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不管是临床研究的挑战与商业化困局,都成了其前进的绊脚石。